空间是城市存在的基本形式,既为形式就势必要依靠人工构筑的建筑、构筑物、雕塑、景观等等构成有一定尺度规模的有边界感的空间存在,比如室内室外,街道亦或广场。又因其使用人群和功能的不同产生不同的空间性质,比如私密的或者公共的。城市空间中面向大众开放的提供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以及开展各类公共活动的空间即城市公共空间。古罗马时期,维特鲁威就在《建筑十书》的第一书第十章里专门论述了如何进行公共空间的定位,“如果城墙靠近海边,那么广场的地点就应该选在港口附近;若是内陆城市,广场就应该居于城镇的正中央”。中国在更早的公元前5世纪《周礼·考工记》中专门规范了周代王城建设的空间布局,“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也对市民生活需求的“市”做出了明确规划。东西方关于公共空间的规划思想,因为社会体制的不同,产生出完全不同的格局和形式。芮沃寿(ArthurF.Wright)认为,中国古代城市在城址选择和城市规划上,“存在着一种古老而烦琐的象征主义,在世事的沧桑变迁中却始终不变地沿传下来”。《考工记》中的城市公共空间显然主要是为了满足基础功能的空间形式,而非促进交往和进行各种仪式活动的场所。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城市空间结构。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大多数公共空间属于官方性质,唯有酒肆、茶馆附带一定的娱乐属性,对普通市民而言,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专有空间是很缺乏的,也不可能有更多的公共文化空间。
中国古代城市公共空间
关于公共空间的定义,目前引用较多的是英国学者马修·卡蒙纳(Matthew Carmona)对其的表述,“公共空间是与所有建筑及自然环境相关联的可以自由到达的场所。”[1]。公共空间具有两种特征,空间物质形态的开放性和空间对公众的开放[2]。中国城市公共空间以街道、市场、公园、广场为代表,但其中大多并不具有当代西方公共领域理论的城市公共空间特征。[3]
“市”由最初郊野自发的,临时的“市”最开始是专门为统治者服务的“宫市”,还不具有公共性。春秋时面向市民的“市”在城市中出现,一直到隋唐时“市”基本以封闭形态为主。隋时实行严格的道路等级体系和“里坊”制度,反映出强烈的“等级”意识形态。唐代集中制高度发展,里坊被坊墙围住,只在规定时间内开放,公共活动空间被严格控制。唐代公共空间中寺观等宗教场所活动频繁,有节日和日常俗讲活动,衍生出买卖行为,寺观园林普通百姓可以参观游赏。唐代的街道小巷可以开展体育游艺活动,例如马球、蹴鞠等,因而街道成为唐最具广泛参与性的公共活动空间[5]。宋是我国城市公共空间定型时期,里坊制被打破,允许市民在街边自由建筑店铺交易,“侵街”行为使街道成为市民主要的公共空间。沿河区域和寺院广场等区域也作为开放式空间满足市民交易、交往和休闲需求。[6]
《清明上河图》中城市公共空间
街道小巷等交通空间
图1 街道小巷等交通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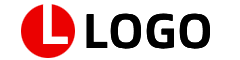
 以《清明上河图》为参照的宋代城市公共空间研究-测试新闻-开封历史地理信息平台
以《清明上河图》为参照的宋代城市公共空间研究-测试新闻-开封历史地理信息平台